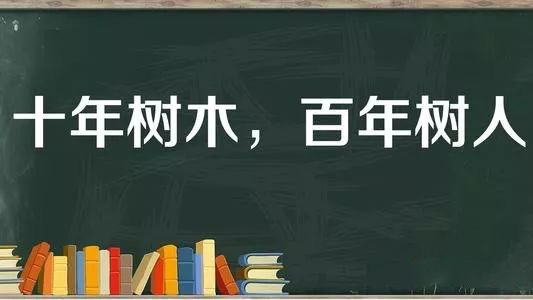一泻千里的儒学发展史:“钱学森之问”之我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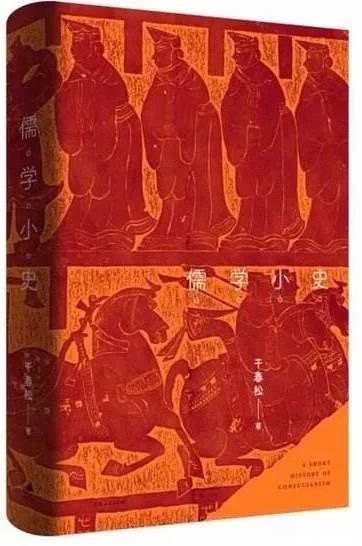
“钱学森之问”之我见
——我读干春松教授的《儒学小史》
一、一泻千里的儒学发展史
为什么科技越来越先进,世道却越来越暗淡?
干春松教授的《儒学小史》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但我很期待!于是我看到了我想看的东西。当然,或许是因为我先有了这个心,所以才会看到我想看的东西。
一路读下来,从先秦读到现当代,“儒之为儒”的氛围越来越少了,而纷争、迷茫、创见、拆东墙补西墙越来越多了。往上走,皆有千秋功德流芳百世,往下看,只见一江春水奔向大海。说到底,“一泻千里”就是我读《儒学小史》之后,对整个儒学发展史的观感。

二、历史上的儒家圣人梯队
回溯历代儒家圣人,或可作为我们对于儒学发展衰落的一个角度。
《易经》有“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位”对于圣人来说非常重要,否则虽有圣人之大器,奈何不得其大用,即便其对于社会风化的改进有益,对于整个社会环境的维护和发展改进必然有限。对于以仁守位、“素其位而行”的儒家君子来说,无所谓大位大用,皆可以“无入而不自得”。也就是说,圣人不在乎“位”,呆哪里都是“大宝”。
那么,谁需要圣人?一个不大会错答案是百姓需要圣人,因为百姓希望得到圣人教化滋养。但百姓自己也没有位,若有,最多也只能为圣人提供一个“师位”,圣人要想建功立业,师位显然有限。
另一个不确定的答案是朝廷需要圣人,因为君王都希望长治久安,借圣人为自己的江山伟业服务。但这个比较难,一是朝廷未必能识别圣人,二是即便有圣人在野,也未必真能得到重用。
选来选去,朝廷多只会选出听话的人,其次是又听话又能干活的人。这里的能干活的人未必是能干的人,能干的人可以指君子,能干活的人就未必了,可能多是表面冠冕堂皇,实则自作聪明、自私用智、狐假虎威、以公谋私的“德之贼也”的乡愿恶人而已。而如果君主不清明,能干的人往往会被听话的人排挤,最终还是无所作为。
圣人无位,在位的又不是圣人,如何是好?
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培养足够多的圣人。这个就更难了!
但并不是不可行!因为这是教育可以做到的,而政治可以决定教育。
只要真想,就没有做不到。
我们来看下历史上儒家的圣贤(不完全统计)。

第一梯队:尧舜、汤伊、文武周公
这可以是儒家圣人中的第一梯队代表人物,都是圣王,如尧舜汤文武;或者是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可以代行天子之职的辅臣,如伊尹、周公。
因为他们是圣人,又有天子之位,所以能施仁政于天下,且能物来顺应,变动不居。文治能远人来服,武功则攻无不克。
他们的言论和故事成为儒家思想的基础。
第二梯队:孔子、孟子
这是儒家圣人中的第二梯队,气氛已经不同了。孔子是形似圣贤而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丧家之狗。孟子亦不过如此,一边是“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的夫子,一边是“王顾左右而言他”的不受重要的谋士而已。两者都是不受待见的导师而已,已经谈不上“位”了。孔子有过一段从政经历,但最终并没有成就大的功业。终其一生,其政治成就尚不如弟子子贡。
孔子是儒家的创立者,而孟子是集大成者。

第三梯队:董子
这是儒家第三梯队代表人物。但已经没有了儒家心传了,只在于政治。董子以《春秋公羊传》为胜,推行“天人感应”、“大一统”思想,在思想上助力大汉政权江山稳固。其同时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使儒家得以在政治上确立了唯一的官方地位,打通了儒生成为官方政治人才的通路,为后世官方取士提供了参照,垫底了儒学官用的政治基础。
董子有十四年的从政经历,也都只不过是汉王朝属下封王的丞相而已,并没有成为汉武帝的重臣。
董子是推动儒家正式登上政治舞台的关键人物,但因为儒家心性功夫已经断了,所以最后儒学变成了士人求取功名的梯子。儒学一边成为正统,一边沦为工具。
第一过渡梯队:文中子、韩愈、李翱
这是儒家第三梯队走向第四梯队的关键人物。
文中子以“王佐之道”为己任,曾效仿孔子续写六经。并由此对前来求学的弟子们因材施教,授予不同经典,为当时的朝廷培养了一大批德才兼备的人才。对于道学多有创新和发挥,启发了后来的宋明理学。
韩愈的文学名头大于道学,核心贡献在佛学泛滥的社会氛围中,坚定地捍卫了儒家的主流地位。他的《原道》至今仍是儒学道统之说的名篇。韩愈对于儒学的贡献也仅止于此,他也只是一个朝廷小官而已。不过,他有一个学生叫李翱,写了一篇《复性书》,挖出了《礼记》中的《中庸》。
据说后世学者对于《中庸》的重视,应该从韩愈李翱师徒始,之所以很重要,因为这是重续儒家心性道统的突破。但二位并没有把儒家心性之学讲清楚。
第四梯队:北宋五子
这是儒家第四梯队代表人物。在前朝儒学衰颓的气象和前人的启发下,邵雍、周敦颐开启了儒学新篇章,他们教出了二程,二程与张载是甥舅关系,五子交相互,多有论道,相得益彰,他们一起重建了儒家性命之学的理论基础,试图接续孔孟,并且直接启发了后来的朱子。

第二过渡梯队:南宋朱陆
朱子一生志在圣学,他精力充沛,心志宏大,气魄超卓,在北宋五子启发的基础上对儒学做了大量的体系化的梳整注释工作,将儒学理论化、规范化的工作。朱子试图解决前人未尽之事,也就免不了要有许多的“定论”和“创造”,于是在往圣经典上动手术,移花接木、查漏补缺。朱子整齐的学问成就得到了官方的认同。
总体上朱子只是个道学家,是个道理大过良心的卫道士。朱子最大的贡献是让儒家经典成为科举取士的标准教材,好处是天下家家学圣贤学问,害处是读朱子学没法开悟,他自己也没有超越,因为他把心性功夫做反了。
陆子是个另类,所学所悟皆是家学渊源。他兄弟多,是个幼子,出生的时候因为母亲年迈,差点被送到乡下奶妈家,因为大哥不忍心,正好大嫂刚刚也生了孩子,奶水充足,所以吃大嫂奶水活命,少了一份人间的离苦。所以陆子不刻板,他对于人间伦理更多一份人情,更通人性。他年少开悟,识得“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他做学问也凭良心,所以白鹿洞书院讲学能把朱子讲哭。他与朱子同时代,他改不了朱子,但也不受朱子影响。
陆子虽然开悟了,但基于与朱子同时代的学术基础,同样没有完成儒学从本体到功夫,从问学到作圣功夫的统一表述。这部分工作,有赖于三百多年后儒学第五梯队的王阳明来完成。

第五梯队:明朝王守仁及其学派
有了北宋五子的启发开辟和南宋朱陆对于儒学的梳整和激辩,在经历了元朝对于汉人及汉文化的漫长萧杀,到了明朝,优秀的华夏文明终于否极泰来,迎来了春天。在吴与弼、娄谅、陈白沙、湛若水等人的启发下,在苦读苦参朱子宏大集注的基础上,在经历常人难以忍受的磨难下,动心忍性的阳明先生终于打通了从陆子到程灏,到周敦颐,一路向上接通了孔颜思孟心性之学、尧舜文武周公圣王之心,儒学从此风景不同!
阳明先生的贡献在于纠正了儒学陷入礼教支离的局面,维护了儒学中正大道的根本,启发学子知行合一,以免沦为“精致利己主义”的伪君子。在朱子学派中,所谓的学养多变成了谋取功名利禄的佐料,而功名则成了许多人为非作歹、为虎作伥的踏板,能走多高就坏多远!在阳明学中,因为事事问诸良心,而不是教条,行与不行由是非之心做主,得之于心者行,不得之于心者不行,善恶由我不由人,简单明了!
阳明先生37岁悟道,57岁去世,也许是走得太早,也许是身体痼疾影响,也许是心性之学本就高明,参悟不易,总之,虽然他终于在学理和行动上都将儒学扳回正道,但毕竟朱子学遗毒甚深,即便是他的亲传弟子,也多有不能规范传承。多少人的一生学问精神都用在争朱陆是非之上,而不能细致深刻体悟阳明先生的一片苦心。先生发现的问题至今犹存,先生提出的方法却鲜有人认真对待。
然后,就没有了然后!
现当代所谓的新儒家不过在儒释道三教中徘徊不前的学问家,不过是好究朱王是非的牢骚家,不过是急于立言著书立说的作学家而已。于儒学并无真的承接体悟,当然也就更少有得大宝之位而行的圣人了。
非常遗憾的是,虽然董子在汉朝就把儒家推上了正统,甚至一千多年后的朱子把儒学变成了官学,至清朝结束累计又八百多年,但有个结果一直都没有改变,那就是自周公以后,华夏都没有出现过真正符合儒家圣人标准的明君圣主,看看上面各个梯队的儒家圣贤就可以知道,他们许多人至多不过是个部级干部!
原因很简单,因为科举取士不过是君主选贤任能的工具,圣贤得不到任用也就很正常了。而皇帝因为有家传的天子之位,则不必是圣贤。虽然也曾经涌现过如魏征、王安石、张居正这类有所作为宰相之才,他们也都是儒家学子,但最终都因为自己圣学功夫不够,圣人心性未见,而未能寓教化于政治,未能将精力放在推行圣学,教化子民上。
如果不是王阳明,儒学不过是个工具,而儒家的圣贤大多不过是一个象征符号!

三、文化是教育的产物
经济社会的发展一直以来都是必然进步的,因为技术一直在进步。技术变革推动经济变革,经济变革推动社会变革,所以这种革新是始终存在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应是今人所共知的公理。
既然这种变革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那么作为影响人的意志的文化对经济社会的发展也就起不到必然的影响,而最多只能是退而居其次,不过是辅助、推动和教化!也就是说,无论哪个宗教或者学派,不管它多么高明,都不可以直接改变社会进程,也不可能真正意义上影响科技进步。
但是,文化做不到的,教育可以做到!
教育的目的和教育的方式会影响科技进步的进程,而教育的目的和教育的方式则由政治环境主导,而不由宗教和学派决定(政教合一除外)。政治环境宽松(比如社会环境混沌/分崩离析;皇帝开明、重视文化或无所作为等),教育的方式就会趋向多元;政治环境逼仄,教育的方式会趋向单一。多元才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单一就只能万马齐喑一个声音。
政治环境对于教育的影响反过来影响科技进步,科技进步决定了经济环境,经济环境最后影响政治环境。同理,是教育的方式影响文化传播,而不是文化影响教育。一段时期内社会文化氛围和质量,大体都可看作是教育的产物。

四、政治环境决定教育
文化对于科技的影响如此,对于政治环境的作用只能是辅助、推动或者说赋能。文化能移风易俗,但往好移是民风淳朴、人心向善,往坏移就民风彪悍、私欲横流了。从这个角度看,文化既有可能振奋人心,也可能助纣为虐。
但文化本身没有指向性,也没有主观能动性。本质上,这一切都是政治作用于教育而导致的,与文化本身没有必然关系。
当年明月在《明朝那些事儿》里面讲到“气数”这个词,令人印象深刻!这本是一个描述天地四时运转阴阳转化的词汇,这里的气是指阴阳之气,数则是阴阳消长的度、频率或周期。
对于天地来说,气数就是四时节气,对人来说可以是命运安排。气数足够,则生机勃勃,虽然遭遇百般摧残千般挑战,仍然能斗志昂扬耸然挺立;气数将尽,即气息尚存,则虽千疮百孔,仍能垂死挣扎,保持一个衰落的气象在;气数已尽,则有一种摧枯拉朽的力量,势如排山倒海,虽有良策天兵,亦不可补救。一如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万物之生发无惧料峭春寒,而秋之萧杀便是势不可挡!
气数对于政治环境来说,就是其由盛而衰的变化。它是一个综合指标,是日当正午还是日落西山,可以通过对各种现象的观察而得出。气数不由文化决定,而是由政治环境决定。若是经济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则政治环境的改变是必然的。这种改变对于江山是姓刘还是姓李的影响相对是微弱的,而对于是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这样的大改变则是巨大的。(前文已经叙述过)
一个朝代的气数对科技进步的影响可能早一百年,也可能晚一百年。早一百年,则多几代人受益,晚一百年,则多几代人受害!(比如元朝、清朝)但一旦气数已尽,环境发生改变,则科技终归要赶上来,而且是会一日千里般的快速地赶上来,推动经济环境的加速发展,如此而已。(比如唐朝、宋朝、明朝)
试看汉唐宋明与元清二朝的差异,这几个时期文化有多少变化?都是儒家道学为主,佛老为辅,但政治环境差异巨大,而文化、科技的发展则有天壤之别,所以归根结底还是政治环境在起作用。

五、浅谈“钱学森之问”
“钱学森之问”的由来太有名,这里就不费笔墨了,但其答案一直是个谜团。在我节日期间所读的《大乘起信论考证》(梁启超著)一书的总序中,作为主编的许嘉璐先生也提到了这个问题。正好写了这篇文章,这里谈下我的粗浅看法。
民国之所以文风鼎盛,大家云集,应该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1、 从明朝以来的小资产阶级工商业的社会发展基础一直没有改变;
这个是物质基础,有丰厚的藏富于民的物质基础(比如各大商帮、票号),才有大量的人才储备条件。有恒产者有恒心,有恒心的人多了,这些人的子弟中读书人就会多,读书人多了,社会文化底蕴就有了。如此良性循环,几百年下来,政府通过科举取士带动,下层地主、财阀、门客、先生、劳苦百姓都努力培养读书人,社会人才储备就更丰厚了。
2、清兵入关以来对于学术思想的钳制导致的长期压抑和1840年鸦片战争促动的民族反思带来的触底反弹;
我曾讲,清廷无圣人,以断国人曾国藩之“半个圣人”的念头。清廷是主子和奴才的文化氛围,人且不是何来圣人?以至于后来的革命要站起来争做个主人。奴才文化并不是西洋文化给我们的,而是满清蛮夷给我们的。给跪主子跪了两百多年的汉人,丢失了传统人文风骨太正常不过。以至于有太平天国、义和团这样失心疯的组织,还能横行一时,不可思议!
虽然如此,儒家经典、圣贤故事中存在的君子之风、圣人骨血并没有被阉割殆尽,一旦清廷气数已经,则“九州生气恃风雷”的基础便有了,汉人终于尝试着站起来说话、昂头挺胸做人了。
3、源远流长、扎实讲究的儒家学养功夫为学人汲取西方新思想、新技术、新方法的迅速掌握和运用奠定了基础;
传承两千多年的儒家文化有一套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这套体系不仅在读书识字上,更重视洒扫应对、克己复礼、断断休休的心性功夫。儒学的教育不同于识字、科学、方法,而是通过洒扫应对做参学悟道的功夫。经过儒家道学打底的学子,再进入西方的学科教育体系,就如海绵吸水一样迅速和饱满。一旦确认某个学术方向,就能以举一反三的思维做人一己十、人十己百的学问功夫,想不出成绩都难。
4、混沌、开放、求新、求进的社会环境,为百家争鸣和一门深入提供了条件;
民国时期的社会环境内忧外患,思想多元,人人皆有向上奋争,变革图强之心。腐朽的清廷终于崩溃了,军阀割据不断,财团商号纷立,革命家此起彼伏,各种新言论、新思想、新技术、新方法都竞相涌现。这实际上是一种压抑良久、喷薄而出的内生力量,一种一元复始、万象更新的气象。
整个社会,特别是青年人终于不必屈膝为奴、能摆脱封建礼教束缚了;饱学之士终于可以畅谈社会理想、建国方略了。更有许多年轻人怀着救亡图存、科学兴邦、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人生志向,“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甚至许多人都秉持着“埋骨何须桑梓地,人间无处不青山”的革命斗志在奔走!这一切,依赖于混沌开放、求新求进的社会环境。
今天,我们要想回答“钱学森之问”有点难,也有点奢侈。因为,环境不是你想就有的。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大清两百年的萧杀气氛和文化沉淀,才有了民国人短暂的文化辉煌。但掘地三尺何其易,拱把之木需三年!树木不易,树人更难!我们经历了土改、文革,贫瘠的文化基础上,今天的我们如何才能找回这个根本?
唯有有识之士得居大宝之位,回溯教育的根本——发明本心,培养圣贤!(不是我们通常所谓的素质教育,今天的素质教育已经沦为职业技能教育)从传统儒学教育上汲取营养,加强青少年通识教育的培养,将国人的心性学养基础储备提前到十五岁之前完成;然后再进行西方先进的学科教育,由学人自由选择学问研究方向,确定人生目标,实现人生理想。
于此同时,全社会要积极开展风化融通的努力,移风易俗,在价值观上做积极规范和引导,充分利用好新时代在基础科技、国民认知上的优势,在信用和法治上做努力,要让仁义之风盛行、君子当道,而功利之风渐消、小人难行。
总之,我想说的是,文化有赖于教育,教育取决于政治。只有明白这个逻辑,我们才有可能回答“钱学森之问”。而文化与科技的关系是土壤和树木的关系,文化能提供基础养分,但打不打算植不植树,把树植到哪里则是教育(园丁)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