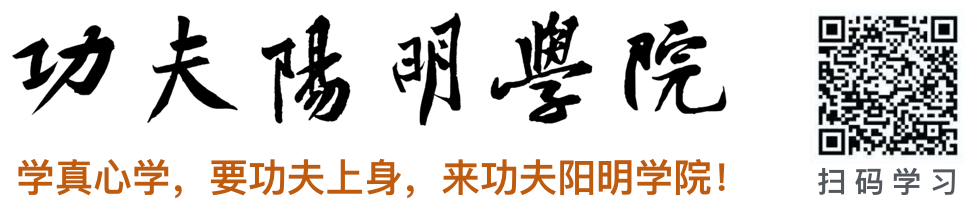丁元英排第四——电视剧《天道》中的人物段位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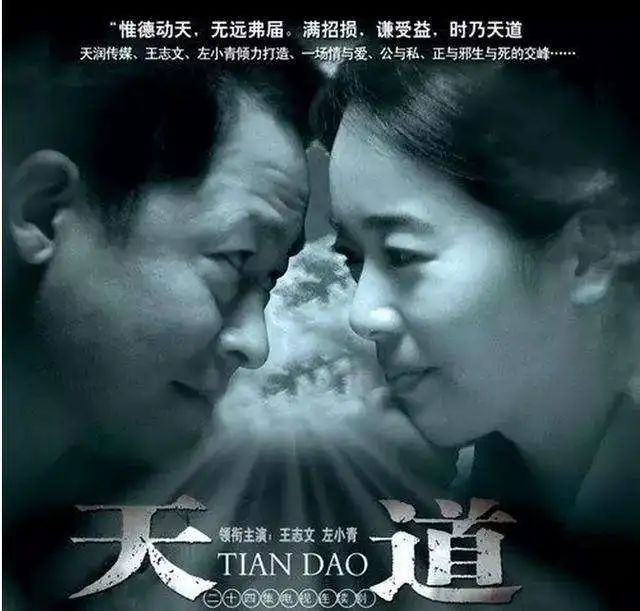
天道剧照
1
不知是否因为我与良知心学关系的原因,经常在视频号、抖音视频中刷到电视剧《天道》的故事片段,其中多是关于主演王志文先生就佛道思想、生意经上振聋发聩的观点。
于是,终于忍不住,我在孔夫子旧书网上淘了一本,书皮上印有王志文和左小青的照片。花了两天的时间,几乎什么也没干,就为看这本书。
现在,趁着余温未退,写点感想。
2
故事明暗两条线,一条是围绕丁元英(王志文饰)这个人物的智慧、心性、对世间乱象的洞察力等等,包括开篇的肖亚文、芮小丹(左小青饰)、韩楚风都是为了丁的出场做铺垫,乃至后面的音响发烧友,都是烘托丁的存在和与众不同,这个是明线。另一条是围绕社会变革中关于生存发展与政策法规,乃至与道德风尚之间的矛盾,丁元英参与的私募基金的股市猎杀,以及其策划的格律诗音响公司扶贫农村,甚至芮小丹的人生志愿、职业选择和最后归宿都无非在诠释这个主题,这个是暗线。
这两条线紧紧围绕丁元英与芮小丹二人的爱情故事展开,从相逢的偶然,到相识的误解,到相知的坎坷,再到相爱的疼惜,最终因为芮小丹因为执行抓捕任务伤残选择自杀告终,故事情节可谓跌宕起伏,心弦紧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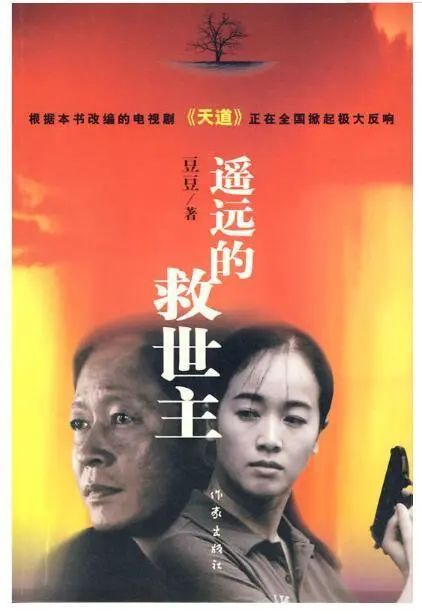
3
芮小丹的自杀很容易理解,活着是为了意义,也可以说是自我实现。如果意义不存在,也就是说期待的自我实现成为了不可能,那么活着也就没有了意义,那么也就没必要活着了。世俗之见(一般意义上看),我们是为了别人活着,比如为了爱我们的人。但芮小丹是通透之人,她明白活着终究是为了自己,而不是别人,即便她深爱丁元英,疼惜母亲,谅解了父亲等等这些,都不足以让她苟且偷生。她要做的是心中的那个自己,做警察如此,去留学如此,选择丁元英是如此,计划不做警察改做文化也是如此。可现在残废了,这些都变成不可能了,她既无法接受自己的不完美也不愿意变成自己所爱的人的负担和拖累,结束生命就是最好的选择。
4
关于天道,在这本书里面有多处描述,且场景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而不同,有红尘对话,有教堂说教,有禅堂启发,有法庭辩论,有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有从社会发展的角度,也有从政策法规的角度,看似妙语连珠,实则多少做作。当然,这是一部小说,自有其想表达的主旨意蕴。但若是论道,就尚隔一层。
书中关于道的表达最经典的就是两句话,一句是在总结马克思主义哲学时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有那么点意思,但不够全面。因为这句话在传统文化范围中,更贴切地是用来形容“天”,而非道。说道则不能离开人,所以言道不远人;说天,则可以无视人的存在,所以言天人合一。
另一句则是“神即道,道法自然,如来。”也有对神和人的存在关系做了阐述,借《圣经》说话。“那么,神是什么?神是不是根据人的需要造出来的?这个就是《圣经》神学理论上存在的问题。《圣经》的教义如果不能经受逻辑学的检验,可能在实践上就会存在障碍。如果经受了逻辑学的检验,那表明神的思维即是人的思维,就会否定神性。换一种说法,神性如果附加上人的期望值,神性就打了折扣。然而神性如果失去了人性期望值,那么人还需要神吗?”
其实,只要“神”是外在的,神就不靠谱,神必是自心良知。道呢?一样,也必是自心觉悟,否则就像大马路,都可以称为道,但实际上人走的才是道,否则只是路而已。这其中的细微差别只有体认者方能察觉。路有千万条,你走的才是道!你若不在道上,就是冥行妄行,则昏昏然已失去自己矣。
如来者,无去无来,似来未离者也!《中庸》言“可离非道”即是如来。
5
小说中将国人具有民族气质的劣根性批评大体可以用“皇恩浩荡”、“期待救世主”两个词来形容,并提出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的概念,认为弱势文化的现实环境无法承载强势文化的竞争手段,言下之意这个弱势文化应该就是指华夏文明,也即是道家倡导的清净无为、尚柔守弱,和儒家提倡的五伦八德、孝悌忠信。小说批评的现象是对的,但显然对儒道两家的思想精髓理解不够。
如果把政治和文化放在一个锅里煮,期待煮出政治的结论或文化的结论都不可能。锅里元素越多,越不可能得出单一的有意义的结论,五味杂陈,便不纯粹,不纯粹便不可能究竟了。只有让政治的归政治,让文化的归文化才能说清楚。如果说文化是土壤,政治是果实的话,那么决定政治的其实并不直接是文化,而是园丁或者说浇灌者,只有当这个园丁或浇灌者是老天的时候政治才是文化的产物,否则,歪瓜裂枣的政治并非天意,而多是园丁或浇灌者的人为。
“皇恩浩荡”是现象,是政治影响的结果,所以子民便有“期待救世主”的心境。但这不是文化的结果,而是教育、宣传的影响。教育、宣传如果服务于政治,那与文化便有天壤之别。就像园丁有随地大小便的习惯,偶然在树下来一泡,不应该也不能算是浇灌和施肥,否则对于树木就是不负责任的。但这样社会现象总是存在,园丁随地大小便只要在情理范围内,也无所谓善恶,但他不能代表文化,也不能承载文化。但如果园丁乃有意为之,则变成人的主观行为,可能是政治手段,但绝非文化使然。
我们的子民是内敛的,这里有文化的成份在,但需要狼性还是需要羊性,则是机制决定的。这里的机制不仅是竞争机制,也有教育、宣传导向。秦国当年为了一统六国,需要狼性,所以给子民以爵位封赏。但六国一统之后,狼性就多余了,所以意欲销天下之兵刃器械而铸金人,而待子民如牧羊。
6
上面就是我读这本小说想说的,接下来对主要人物做个段位排列:
肖亚文,段位:如来,所见即所得。肖亚文一直按照自己的良知去做事,从她毕业后选择打工,遇到丁元英,后来追随丁元英。虽然中间有一段时间离开丁元英,但始终相信丁元英,并全身心(全部身家)投入到丁元英策划的事业中去。一个信字诠释一个诚字,一个诚字铭刻一个信字。《中庸》谓“诚则明”即是,“自诚明,性也”。
芮小丹,段位:须菩提,坚定不移做自己。芮小丹内心始终有个自己,只是一开始并不自觉,后来经过丁元英的启发,才逐渐觉悟。她因为父亲抛弃母亲而变得叛逆,总是作出与父亲相背离的人生选择,其实就是想做自己。在遇到丁元英之后,发现真正的自己并不是一个职业选择,不是做什么或不做什么的问题,而是是否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问题。觉悟之后的芮小丹重新规划了自己的未来,也能够自如地融入到生活和工作当中,以丁元英女友的身份招呼客人吃饭做菜,以“夏雨”的身份扮演二奶完成工作,乃至最后因为偶然遇到逃犯而奋不顾身而导致伤残也不后悔,果断地选择了自杀结束了生命。生命的意义就在于此,活着是为了成为最好的那个自己。如果那个自己不存在了,活着的意义也就失去了。这就是丁元英说的“当生则生,当死则死,这丫头不简单啊”,这虽然是旁观者的话,但也是对芮小丹最高的评价。
欧阳雪,段位:菩萨,慈悲没有我执。欧阳雪因为芮小丹结识丁元英。自始至终对于丁元英言听计从,且没有任何条件和要求。对于自己的能力边界有清晰的认知,从不越界。对于合作中出现的意外事件,虽然心里不认同,但都能担当接受。
丁元英,段位:罗汉,无分别心但有我执。丁元英是整个故事的第一主角,小说中所有的人、故事都是来烘托他的,个性、不给别人添麻烦、洞察力、运作能力、算计,活在自己预设的世界里面。读完通篇故事,感觉丁在计谋上有点诸葛亮的味道,但他没有一个忠于的对象,如果说有,他忠于的是“道”。这个道没有善恶,没有分别,只有角色,参与其中的都会被影响。但丁身上少了什么?仁慈。道没有善恶,但人有性情。人与人之间如果只是无情的道,那么弱肉强食就成为天则。但其实不然,有了仁慈的道便不同,就是人道。包括芮小丹的同事、芮小丹的父亲对他的不满,抱怨他为何会在芮小丹最后给他打电话的时候没有说话,在这一点上,丁有点自以为是——以为的道,少了人情味儿。至少丁可以讲一句:“你当心一点!”“一个人别逞强!”“拖住对方,等支援!”之类的话,这些话不碍芮小丹作为警察的身份,不影响其继续执行任务。当然,芮小丹的结局也是作者为了烘托丁元英这个角色“在道上”的“通透与无情”的。
这让我想起了日本侵华,日本政客以大东亚共荣圈为标榜,所到之处,无恶不作,民不聊生。仅在我国,就犯下了殖民台湾,控制东北,制造南京大屠杀,细菌战、731部队的人体试验等等罪行,与德国意大利法西斯阵营狼狈为奸,最终招来中国乃至整个亚洲人民的强烈反抗,而终于臣服于美国人的两颗原子弹。这里面的逻辑似乎有点相同,就是只有所谓的“道”——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少了仁慈。日本人为了自己民族的利益实施对外扩张,从本民族长远发展的角度是可以理解的,但其以杀戮、灭绝、歇斯底里等不顾人性的做法是令人不齿的,最终的结果是两败俱伤。
丁的不见道,我们从丁得知芮小丹去世吐血这件事儿就知道。丁实际上一直活在自己设计的环境里,比如对于音响的高标准高要求,对于生活的极简主义,对于工作的狂热主义,这个环境并非真实的现实世界,而是被设计过的。丁做私募玩金融和策划格律诗做商业也都是如此,甚至包括他跟芮小丹的爱情故事,也都有某种精心设计的痕迹。比如,他们一起去耶路撒冷,芮小丹当时是本来没打算去的,丁主动参与与芮小丹一起完成了这件事儿。
丁的无分别心体现在不分对象都如此,凡是参与到他的设计中的角色,一网打尽,寸草不生。丁的我执则体现在对于无情的道的自以为和坚守,他以为他看到了根本。就像他说的那句话“神即是道,道法自然,如来。”这句话放在这里好像融会了各家各派,基督、伊斯兰,乃至儒释道,实则并非如此,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失去了仁爱、慈悲的道,都已不是道。

任何人或民族,只要少了对被征服者的仁爱和慈悲这一点,就要出大事。犹太人的精明、日本人的冷酷、欧美人的傲慢,尽皆如此!中国人的内敛就是因为多了人性,多了“不忍人之心”,看似懦弱,看似如书中所说的“弱势文化”,实则是真正的大智慧,所以总能反败为胜,虽社会发展起起伏伏而文化则长盛不衰,就是因为在道上。
就像肖亚文相比丁元英,自始至终都是丁元英强而肖亚文弱,但全胜者是肖亚文而非丁元英。丁元英实际上总是以一种精明、冷酷、傲慢在设计一个局,最后他自己其实也在局里面,并非局外人!所以他会在私募基金宣布解散时收到来自朋友的不信任反对票、被詹尼限制资金使用,在格律诗公司发展过程中出现冲突时被来自各方面的人不理解,乃至林雨峰会持枪登门。一旦这个设计破局了,最受伤的还是自己。设计者成为局中人是不可避免的事情,搬石头砸自己的脚,还有自以为高明。只要有设计的痕迹,高明就是做作!既然做作,就是不见道。
说丁元英是罗汉,其实还是高看了他,其实更贴切的应该是修罗,或者说精灵。
韩楚风,段位:智者,知进知退,见好就收!韩这个角色在全书就是来衬托丁元英的,其几次出场皆是如此。韩能听得进高明意见,善于笼络人心,韩的稳重、实际是涵养使然,而大方、风度则是地位所赐。
王明阳,段位:氓流,就怕流氓有文化!王明阳这个角色的出现纯粹是为了烘托丁元英对与信仰的理解,借芮小丹的口说出来而已。王明阳并不高明,只是有墨水的坏人而已,而且已经坏透了,这就像儒家的乡愿者。实际是得了空心病的人,找了一个愤世的理由和伪装的事业做依托,其实灵魂没有着落,更不知道自己的心要如何安放,所以能杀人不眨眼。芮小丹并没有解救他,不过是给他本来空洞的心塞进去一把泥,夯实了而已。王明阳以为自己精神上吃饱了而已,其实他哪有信仰?
叶晓明,段位:聪明人,担不起风险的投机者!叶晓明从一开始就在找机会找出路,他是最早发现丁元英不普通,但又随时都有自己的一番主意。始终认为丁元英是格律诗和王庙村的局外人,可不知道这个局的操盘手就是丁,这在外人都一目了然,而叶则被私欲障目,最终因为自己的小聪明而让自己玩出局。他联手冯世杰和刘冰要挟欧阳雪,让欧阳雪一个人背了几乎全部风险,这是聪明人才能走出的下策。欧阳雪因为心中有正义,有信仰(善),以及对丁元英的绝对认同,所以,一路遇魔杀魔,逼着自以为是的林雨峰作出打败官司就跳楼的夸口,收回叶、冯、刘三人的股权,以一个完全外行的挂名董事长打了个大满贯,全凭赤诚与无私。
冯世杰,段位:老实人,向往美好又不能自主者。冯没有读书,少了眼界。希望能够带领大家致富却没有方向,更没有方法。他只有折腾,不断的折腾,就像不会游泳的落水者试图抓住任何救命稻草一般。他通过叶晓明认识了芮小丹,然后抓住了丁元英这条线。但是,因为没有眼界,没有自我判断,在关键时刻,即使明知格律诗的利益与王庙村的利益绑在一起,也仍然听从叶晓明的话作出了退股的决定。在这个时刻,他内心是不安的,他只能尽可能地为老乡们争取利益,但他没有勇气,阻止叶晓明的自保,似乎他们是一条绳上的蚂蚱,只是他们忘了是谁给了他们爬绳的机会,这条绳牵在谁的手上。
刘冰,段位:小人,慕虚荣而无节操者。刘冰从出场就是个垫底的角色,活在假相、虚无和私欲当中。他不能脚踏实地,为了赚钱没有底线,他抖手白纸、纵身跳楼的结局看似被丁元英设计,实际上是他咎由自取。
7
众生多是看热闹者,不知其所以然,只外在炫目的角色扮演和故事设计就足以让人瞠目结舌,实在里面玄机多未经推敲,只要一仔细就能看出破绽。站在良知心学的角度看,作品中关于道、宗教、政治、法律和市民精神的解构,其实多不究竟,甚至明显作者误解了儒家精神,更不知阳明心学为何物。
电视剧比小说好看,小说比电视剧细腻。但看了小说在看电视剧便多了演绎成份,已经有了导演和演员角色的重新解构,与小说的生命其实是另一番风景。但是,仔细看小说,便知其做工精粗,意蕴深浅。总之,《遥远的救世主》离一部上乘的作品还有差距,但作为迎合时代精神和市民口味的作品还是值得一看的。